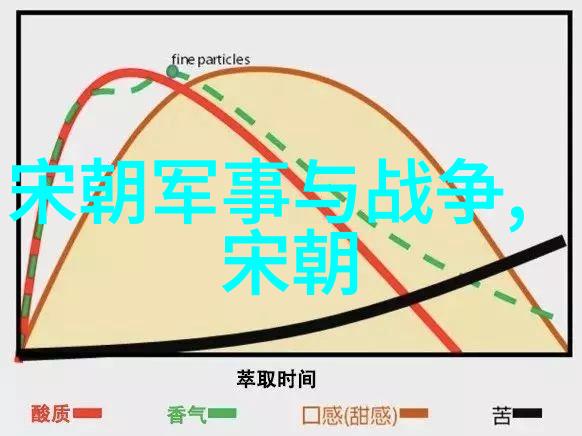郑和下西洋见证了中国古代海洋探索的辉煌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文明。古代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有赖于亚欧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新时代的正是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亚欧的大河与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而在诸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就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只不过互动的中心一直在亚欧的交通上。

自古以来,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着便利,沿着陆上的道路,东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续不断地接触、互动和融合,历时数千年之久。“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根据《史记》的记载,这一词汇出现在张骞生活的时代。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西域”得到极大的彰显。此后广义的西域,所指就是亚欧上几大文明的接合处,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当时文明互动的中心。就狭义而言,西域是一条通道,一种途径,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身至波斯湾头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
尽管汉代已开始了向南海的探寻,但是相对陆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汉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径。唐代以后,虽然海路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没有发生海路交通上升为不可逆转的东西方交往主要途径的改变。最有力的例证,来自成吉思汗以军威建立的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当时海陆交通并举,尤其陆路交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畅达程度。马可·波罗自陆路来华,自海路返回。明初吸取元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派出大规模使团时也是海陆并举。洪武年间陆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刘时勉等人;永乐初年陆路有陈诚等人,海路有郑和等人。
然而相对海路而言,陆路却显然逊色多了。对于海路功绩的认识,有诗为证。明宣宗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样,下西洋是以国家行为使海上道路畅达,由此,“西洋”在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彰显。
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一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西洋”一词,在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在元代,以东西洋并称。明初修《元史》,没有出现此词。词汇涵义的演变和凸显,是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其后“西洋”新名词出现,不仅广泛流行于社会,而且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形成一个象征整合的意义,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国、外国之义。此后,明朝人甚至将亚欧上的撒马儿罕也称作“旱西洋”。下西洋赋予的“西洋”一词的新义,即使在后来西方人东来后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流行于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下西洋的深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的大航海活动,“西洋”凸显,对“西域”形成了压倒优势,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断上升,出现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此后,中国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强劲的态势,决不是朝廷一纸禁海令所能阻隔的。这里还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兴起以后,即使在它极为兴盛之时,也没有多少国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往,自古以来就是以外人来华为主。陆上丝路的象征符号是骆驼和胡人,这是最好的证明(参见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径,情况就更是如此。迄明代以前,有名有姓的出洋人屈指可数,至唐代大都是佛教人士,宋代出洋人几乎不见有名姓者流传下来,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迹才见流传下来。
明初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出使记录《瀛涯胜览》中记载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场景,七下西洋人数最多时达到二万七八千人,频繁的出使无疑使更多国人了解了海外。下西洋后,“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很快兴起,沿海人民开始较大规模走向南洋,留居海外的中国沿海居民日趋增多,他们参与了开发南洋,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上活动——郑和下西洋肇其端的。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
人类历史发展到15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海上运输日益显示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优越性,贸易的需求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所在。明王朝建立后,以强盛国力为后盾,郑和七下西洋,持续近30年的航海经历,为人类交往打破相对分散和隔绝状态,迈出了从陆上向海上转折的重要一步;作为人类交往史上从陆向海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更推动人类文明互动中心从亚欧转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了一个世纪,为15世纪末东西方文明在海上汇合、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奠定了基础,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这首先要从郑和船队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也是一支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官方国际贸易商团说起。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质需求,从远古时候起,“宝”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郑和船队出航的大船称为宝船,顾名思义,是出洋取“宝”的。曾经在明宫上演的《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杂剧(明赵琦美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四集》76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其中将出航目的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和番”和“取宝”。对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后人虽为之揣测纷纭,争论不休,但明朝人是如是看的:“和番”与“取宝”。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和番”就是和平地与海外各国交往;“取宝”,则说明物质欲求构成下西洋的根本原因。这在明钞本《国朝典故·瀛涯胜览》马敬《序》中,有更明确的表达:“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易。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
郑和七次率领的庞大船队,是和平之师、文明之旅,船上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与欢迎的丝绸、瓷器、药材、铁器等物品,船队所至,大都是当时各国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每到一地,他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明朝皇帝的诏谕,表明中国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遍谕国人来与中国船队贸易,郑和等即用宝船所载各种货物在当地进行互市交易。这种通过互市方式进行的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信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平等贸易,由此,下西洋成为永乐年间几大工程中惟一有进项的工程。关于郑和一行的大量海外贸易活动,《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亲身所到20个国家,除了那孤儿和黎代两个小国记“土无出产”外,其他18个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有产品、流通货币、度量衡、市场价格以及交易情况的记述,对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的贸易场景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
同时,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详见日本学者家岛彦一《郑和分(舟宗)访问也门》,《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第55—56页)。郑和远航与满剌加有着特殊关系,自第一次下西洋开始,中国——满剌加——古里是下西洋的主导航线。七下西洋,郑和每次必到满剌加。满剌加国王曾多次亲自前来中国,永乐九年(1411年)的一次规模最大,由拜里迷苏剌国王亲率王妃、王子和陪臣540多人来访。而永乐皇帝也曾赠与国王船只“归国守土”。两国建立的上互信、贸易上互利的友好关系,成为历史上国际关系和平发展取得双赢的成功范例。郑和到满剌加,给满剌加带来了无限商机,满剌加国王同意郑和在其国土上建立货场,用来存放货物,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都汇合在满剌加,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满剌加从“旧不称国”、“人多以渔为业”的渔村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一个大集市”,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繁荣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西方航海东来,才结束了它的黄金时代。
1511年葡萄牙果阿总督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说:“我确实相信,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在我们所知道的以外还有另一条航线的话,那末他们必然将寻找到马六甲来,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说得出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格雷·伯奇编《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述评》卷3,英文版第118页)。通过贸易活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进行着。从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东方记》记述的长长的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商人名单,可以知道满剌加作为东西方文明互动中心是名副其实的。郑和七下西洋,促成了满剌加的兴起,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从转移海上。满剌加的崛起,就是东南亚的崛起,也就是海洋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从陆地向海上的不可逆转的重大转折,导致了自古以来位于亚欧的文明互动中心迁徙到海上,完成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空间转换。人类历史不是开始于一个整体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是人类文明史极大发展的结果。
正是在15世纪出现的东西方向海洋不断探索的进程,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在15世纪初,史无前例的郑和七下西洋,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从“西域”到“西洋”,标志中国对外交往发生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也标志人类交往发生从陆上向海上的重大转折,促成世界文明互动中心脱离了亚欧,转移到海上;一个海洋的时代宣告到来,也最终决定了世界的走向。到15世纪末,葡萄牙人航海东来,无独有偶,登陆地正是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也即卡利卡特。随后,葡萄牙人沿着郑和的海上航线,追寻到马六甲,东西方在海上汇合,一个整体的世界在海上形成。就此意义而言,郑和远航是古代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