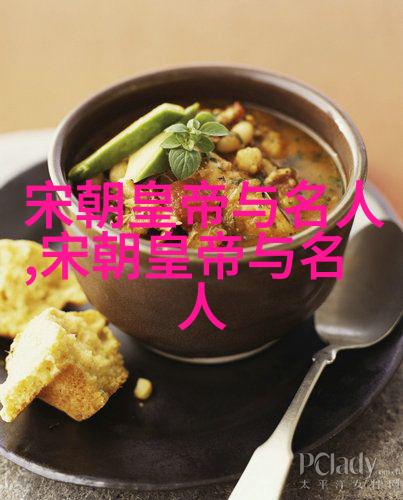朱元璋的智谋如同天书绑缚进京策一出仿佛举世无双
明初,朱元璋发动了“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作为司法改革的旗手,以行政手段来改造司法,发动旨在重新整合社会的清洗运动,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社会监控网络,是朱元璋惯用的手法。《大诰》虽继承了这一特点,以案例和俗语讲述的形式编写,但究以严惩为主旨,血腥味十足。

《大诰》初编第五十九条乡民除患内:“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不畏死罪,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全族诛杀。此乃城乡贤良豪杰绑缚进京的配套制度。
《大诰》续编将范围扩大到一切扰民之徒,而且只赋予高年有德的耆民,不再是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此乃更为明确:“……贪婪之徒,如往常不畏死罪违旨下乡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市井中高年有德耆民拿赴京来。”但律不许赴京越诉,所以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大诰》三编中的条目才不断被载入新颁的律令之中。但到三编发布时,被恶意利用的绑缚制度已十分普遍,因此在三编中特地将“臣民倚法为奸”放在第一篇,列举各种钻营绑缷条典型案例共计18个。

从三编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帝王“拍脑袋”决定后的结果,比如常熟农人陈寿六因受县吏顾瑛欺压,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但其行为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即没有年高耆老,也没有豪杰,而且没有邻人做证。此案竟然由朱元璋亲审,并未通过通政司,这显示出该政策执行上的问题。最后竟知照下面官吏,“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即使陈寿六违法,可不受一般审判程序管束,由朱元璋自己审理。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调整政策方向,从最初的一些激进措施逐渐走向更加合理化与规范化。
然而,这种铁腕治吏的手段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最终仍旧难逃失败。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本应由胥吅承担的大量基层千头万绪的事务依旧存在,而胥员却因为其权力太过膨胀而成为帝国另一极端的问题。而到了清代,更是出现了大量虚职且腐败现象,使得这个系统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以根治。这也揭示了仅靠单纯的手段或政策无法根本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而需要系统性的改革与创新思维去应对这种长期存在的问题。